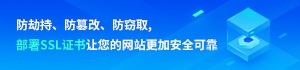《戏剧》2021年第1期丨傅谨:“现代戏曲”与戏曲的现代演变
点击上方“中央戏剧学院”进行关注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AMI”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识别下方二维码查阅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现代戏曲”与戏曲的现代演变
傅 谨
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现代戏曲的“现代”不是时间范畴,也不是题材选择,不应是现代思想的宣教工具,不应是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而是具备现代性品格的戏曲创作与演出。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戏剧转型时试图用散文化的话剧取代韵文式的戏曲的努力未能成功,戏曲现代化的重心才转向对戏曲的改造。一个多世纪来,戏曲在艺术形态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它从广场和厅堂艺术转换为剧场艺术,由此促进了戏曲剧目的整体性倾向和精致化追求。这些改变或有现代性内涵,但只有在坚持戏曲化的前提下才具积极意义。而要确保现代戏曲仍是戏曲,对现代性的多元阐释是不可忽略的前提。
The “modern” in the term modern Chinese opera does not come into the domain of time. Modern Chinese opera does not only refer to operas created in modern time, and should not be a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tool for modern thoughts. Actually, it is not onl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but also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opera with the features of modernity. Bu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opera is not dramatization. The artistic form of Chinese opera is like a verse with strict rhyme.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place Chinese opera with prose-style drama, but failed. Then,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operas has been launched instea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artistic form of Chinese opera is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rt of square and hall to the art of theatre, which leads to the tendency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refinement of Chinese opera repertoires. However, these changes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only because of the premise of insisting o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opera.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modern opera is still Chinese opera,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is the premis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关键词丨Keywords
现代戏曲 现代戏 现代性 新文化运动 张庚
modern Chinese opera, modern drama, modernity, New Culture Movement, Zhang Geng
有关“现代戏曲”和“现代性”,争论多年。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其实它包含了多个人们未必都清晰地意识到的分枝话题。比如戏曲什么是现代,为何要现代,如何才现代等等。在有关现代戏曲的讨论中,更有意无意地掺杂了对传统戏曲诸多误解。如果能对戏曲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其近现代以来的演变有更多分析与认识,廓清迷局,厘清思路,或能对这一难题的解决起到一点推进作用。
一
如果把“现代戏曲”看成是一个有学术或艺术意义的范畴,那我们首先要排除两种基于字面的解释,一是把“现代”当成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一是把现代戏曲混同于“现代戏”,即把“现代”当成一个题材概念。
首先,如果把所有“现代”创作的戏曲剧目都称为现代戏曲,无论将其起点界定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任何时间点,都很难有深入的讨论。按年代界定现代戏曲,纵然可以通过现代戏曲和传统戏曲或古典戏曲的对举,透露出些许与现代相关的戏剧特性,但是从根本上说,机械地以时间划分现代戏曲和传统戏曲/古典戏曲,并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因为从这样的划分中,看不出两者是否具有或具有哪些质性的差异,更何况对戏曲而言,用年代分阶段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是戏曲不仅是创作更是演出,假如现代创作的戏曲作品就是现代戏曲,那么我们将如何定义现代演出的戏曲作品?假如说现代人创作的戏曲就是现代戏曲,那么,有什么理由否认现代人演出的戏曲作品就不是现代戏曲?面对传统戏在舞台上大量上演的现实,用时代划线分现代与非现代的方法,实有先天的困难;即使在现代这个时间段里创作的戏曲作品,其性质亦千差万别,同样是易俗社的创作,既有《三滴血》也有《柜中缘》;同样是成兆才的作品,既有《杨三姐告状》也有《马寡妇开店》;同样是程砚秋首演的作品,既有金仲逊的《荒山泪》,也有翁偶虹的《锁麟囊》,它们从戏剧内涵到艺术形态相距太大,其中固然有些作品确实颇具时代特性,但亦有不在少数的作品仍被通称“传统戏”。就以梅兰芳而言,他的那些古装新戏究竟与时代有多大关系,也很难分辨。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推翻帝制、1912年和1949年两次重大政权更迭,对戏曲的影响固然不能忽视,然而艺术本身的变化,毕竟还需要从艺术内部去考察,仅仅着眼于外在的时间节点,恐怕无助于现代戏曲的讨论。
其次,如果简单地把“现代戏”看成是现代戏曲,同样会陷入理论的误区。
追根溯源,“现代戏”这个概念源于1949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断裂,它导致新社会与传统戏曲之间前所未有的剧烈冲突。梅兰芳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样的断裂对京剧乃至戏曲的整体影响,他说:
解放之初,我将要作一个短期演唱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剧本拿出来审查一过,觉得满目全非,真想一火而焚之。后来在里面勉强挑出三五出,经过了部分的修改,总算是对付过去了。以后唱一次改一次,改来改去,有了新的理解了:我觉得所谓毒素,是含在骨子里而不是在表皮上的,决不是喊一声“天哪”、叫一声“万岁”,来跪拜,念一句“圣旨下”就算是毒素;相反的,加了些“为人民服务”“反对帝国主义”等等的名词,在小丑的京白里念出来,虽然勉强过得去,但是总觉得生硬不调和,大可不必。[1](P148)
全国各地数十万戏曲艺人面临的困境要远甚于梅兰芳。“戏改”初期全国诸多地区禁演数以百计的传统戏曲剧目,导致普遍出现“演出剧目贫乏”的现象,充分说明按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加以衡量,绝大多数的传统戏都与之不相吻合,无法起到建构新文化的积极作用,因此提倡新的创作,就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古为今用的《逼上梁山》模式受到“反历史主义”批评之后,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具备新思想的现代戏,就成为题材上几乎唯一的选择,然而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对现代戏的强力推广之所以在1958年、1964年重复出现,就是由于同样的背景—执政者对传统戏与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格格不入、却又持续占据着演出市场主导地位的状况强烈不满。新政权的文化管理者原以为既然解放后新社会的普通观众觉悟大幅度提高了,将会自觉地摒弃传统戏并转而喜爱具有新思想的新剧目,让新戏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地取代传统戏,然而从1949年至今,这一想象从未变成现实,只有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下,才有通过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现代戏创作的措施。因此我们看到,对现代戏的倡导始终内在地流露出新政权的文化管理者,对有新思想的新剧目无法赢得演出市场上的主导权的焦虑感。传统戏与新剧目一轮又一轮的博弈,最终迫使文化部1964年下令将所有古装戏、尤其是传统戏逐出舞台,为现代戏让出戏曲舞台,才有“样板戏”独霸舞台的现象,这样的政策指向,当然不仅仅是对现实题材的偏爱,更重要的是戏剧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的强烈诉求。
诚然,如同我在此前多篇论文所指,现代戏这个概念从它被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有特指的,不能简单视为现实题材戏曲剧目,更与戏曲史上诸多时事剧有明确分野。现代戏从来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一直被限定在符合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题材剧目范围内,而不是笼统地“反映现实”。数十年来,不仅民国时期那些极受欢迎的反映城市中下层市民生活的家族伦理题材剧目从未得到提倡,当下生活现实中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更是现代戏创作的禁区。当1963年柯庆施提出要“写十三年”时,他绝对不是要鼓励像改革开放后的豫剧《谎祸》和近年创作的京剧《陈毅回川》这类作品,这十三年国民经济多次陷入困境,民众经历的劫难,大量社会精英遭受非人道的迫害,这些不折不扣的现实题材都不可能是他所要鼓励的现代戏的内容。柯庆施强调“写十三年”是“我们要使戏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就一定要大力提倡反映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剧,积极地去表演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热情地歌颂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2]在提倡现代戏的整个语境中,从1949年直到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用词方式或有差异,戏曲作品中体现的主题和思想倾向都是隐含着的前置条件。所以1964年北京举办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的几乎所有相关文献,都声明这是一次“革命现代京剧”的会演,而非抽象的“现代京剧”。柯庆施更特别指出:“同样是提倡现代剧,仍然有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别。” [2]在所有提倡现代戏的政治话语中,这种政治限定始终不曾松动。因此,现代戏和现代戏曲虽只有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更何况现代戏曲何尝不能是古代题材?
既然现代戏曲之现代既不应是个时间概念,亦不该是题材概念,它是否应该指启蒙意义上的“现代性”?
回到有关现代戏的话题,把现代戏和现代戏曲完全对立起来当然是不客观的,至少是在主观动机上,从柯庆施到江青,或许都存在有意识地要让现代戏成为现代戏曲之典范性文本的初衷,既然新思想是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潜在的限定性要求,而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由于明显有异于传统思想,很容易被理解为传统的对面—现代,按这样的逻辑,革命现代戏本该具有最彻底的现代性。在这里,关键不在江青推行的思想是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脉络相一致,是否与始于西方文艺复兴并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后臻于成熟的“现代”观念相吻合,而是假如把现代戏和京剧革命看成是现代戏曲甚至是戏曲现代化的成功标本,显然忽略了现代戏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样板戏为终点的现代戏,从不讳言让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意图。这就把有关现代戏曲的话题自然地引入了另一个方向—用戏曲作为宣教现代思想理念的工具,是不是它就成了现代戏曲?众所周知,视文艺为宣教工具的理念毫无现代性可言,将戏曲当成宣教工具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中有丰沛的资源,它实为“文以载道”和“高台教化”的当代变体,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还要加上一句“可多识乎鸟兽草木之名”,其工具论立场可谓昭昭,如高则诚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更何况如果戏曲被用以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教工具就是传统戏曲,用以为宣教启蒙思想就成了现代戏曲,那艺术的现代与否,就只成了宣教什么的区别。将文艺作为启蒙宣传之工具,是新文化运动埋下的根子,它在样板戏的实践中达到顶点,至今阴魂不散,只是换了个马甲而已。
中国传统戏曲之要转型为现代戏曲,不仅不是把戏曲从“宣扬封建主义”的工具变成现代思想宣教品,在根本上说,工具论反现代性的本质毋庸置疑,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现代戏曲都不应该仅仅是宣教品,哪怕它宣教的是“现代”思想。
最后值得讨论的就是现代科技手段在舞台上的运用和西方乐器加入戏曲乐队。清末民初以来,各类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等大量应用于戏曲舞台,带来新颖的艺术欣赏体验;晚近又加上更多如LED屏幕和投影技术等科技手段,还包括唱片、影视和互联网等新的技术传播方式。如果这样传统戏曲就演化成了现代戏曲,有关现代戏曲的讨论就显得可笑至极,这些外加的科技手段只是被叠加在戏曲之上,并未改变戏曲质的规定性。至于西方乐器的加入以及戏曲乐队的交响化改造则稍显复杂。西方近代交响乐在人类音乐文化发展中有重大贡献,20世纪西方近代音乐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戏曲音乐吸收西方音乐思想理念并且借用西方乐器,实为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要把这样的学习、吸收与借用定义为戏曲的现代化仍有困难,戏曲乐队不会因加入了小提琴就变为现代,就像交响乐不会因为加入了唢呐或二胡就变为传统。至于交响乐化的戏曲音乐写作,其得失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将戏曲音乐的交响乐看成现代化标识,太容易给人以将现代化混同于西化的印象。如果真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之分,那也不在乐器,戏曲音乐也不会因为借鉴了交响乐的体例与写作方法就获得现代品格。
总之,我们在讨论现代戏曲的定义时,需要排除上述四种简单化的思路,一是将现代仅仅看成时间范畴;二是把现代戏和现代戏曲相混淆;三是将现代戏曲当成现代思想的宣教品的工具化倾向;四是将现代科技手段或西方乐器应用及戏曲音乐的交响化当成现代戏曲的标志。有了这四个前提,有关现代戏曲的讨论才能回到正轨。
二
既然我们要在艺术的层面上讨论现代戏曲,就必须把重点放在艺术形态层面,可惜多年来有关现代戏曲的讨论,极少涉及戏曲本体。假如戏曲不是在艺术形态上与传统戏曲发生了质的差异(无论是否被描述为“进步”),就永远都无法成为现代戏曲。
吕效平大约是少数真正从戏曲的艺术形态、尤其是从当代戏曲文体出发分析并界定现代戏曲的学者之一。他在批评前人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戏曲的现代性追求的漠视时写道:
理论认识上的糊涂状态,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情感上对于“民族性”和对于“现代性”的冷热失衡造成的。例如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就放弃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批判的责任,把古典地方戏特征夸大为全部戏曲的永恒特征,而对其文学性与思想性的贫乏没有丝毫的反思,对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所代表的文学精神与批判精神退出中国本土戏剧的过程与必然性也没有丝毫的反思。这样的戏曲理论,当然不能认知当代戏曲创作主流文体中文学性回归的本质意义,不能辨析当代戏曲作品文学性的现代性特征,也不肯承认古典地方戏乃至古典戏曲的终结,而宁肯把谭鑫培、梅兰芳与陈亚先、魏明伦、郭启宏稀里糊涂地看作一回事,不愿分析陈亚先、魏明伦、郭启宏的现代性本质,更不愿接受这种现代性本质获得的前提恰恰是对于谭鑫培、梅兰芳的革命与超越这个事实。应当看到,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热情往往片面夸大民族文化中的局部现象,而悖离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最终走向自己初衷的背面。以京剧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并不是古典戏曲的全部,它的辉煌恰恰建立在部分地放弃与悖离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的艺术原则和艺术精神的基础之上;在陈仁鉴、陈亚先、魏明伦、郭启宏对于古典地方戏的革命与超越中,却有着对于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的回归与继承。当代戏曲创作的主流文体,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与全部戏曲的古典传统血脉相连。[3]
他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段话里明显的自相矛盾,那就是,如果陈亚先、魏明伦、郭启宏等人的戏曲剧本创作的特点就是努力回到“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的艺术原则和艺术精神”,为什么要把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而不称为回归古典?(我们总不能把从元杂剧直到清初的中国戏曲史说成戏曲现代性的历史)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吕效平指出“剧场的情节整一性原则”是现代戏曲的特征,然而正如他所说,这一戏剧文体特点并非源于西方现代戏剧,而恰恰是欧洲传统戏剧情节样式,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欧洲传统戏剧情节“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为‘现代’的呢?”他自问自答:“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便是克服古典文化的封闭性、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我相信他做出这样的回复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无法再自我追问:为什么中国戏曲不直接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走向现代戏曲,而只能与西方传统戏剧相结合?或许他还可以勉为其难地继续作答,西方的传统对中国而言就是现代的。好,我们已经在这里嗅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西方中心论的气息,而且,这里谈的不是思想层面的人类发展,是戏剧形态的演变。
对,吕效平是敏感的。他的观点浓缩了晚近半个多世纪有关现代戏曲的想象,就艺术形态角度看,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的话剧作品始终都是现代戏曲的目标与支柱。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内在地包含了推动中国社会乃至所有文化艺术门类现代转型的诉求,用新剧取代旧剧就是其明确主张之一,而从五四时期有关“废旧剧”的呼声直到只把话剧看成“现代戏剧”的观点,都不认同戏曲这种艺术样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而既然只有外来的话剧才“现代”,戏曲之获得现代性的道路,就只有学习和模仿话剧。最早提出“旧剧现代化”的张庚说:“所谓改革旧剧并不单是在形式上,而主要的是使它的形式能够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的现实,并且能够从进步的立场来批判并改造这现实。”[4](P242)在他的表述中,旧剧的现代化显然不排除戏曲形式上的改造,只是说不能只止于形式,至于如何改造,其范本与标的是什么,此时的张庚还说得不清楚,然而从他的知识背景看,大约也只有话剧。
这也是“戏改”初期很快出现大量“话剧加唱”的戏曲作品的原因,而在有关戏曲现代化的风潮中,多次出现过以话剧改造甚至取代戏曲的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戏曲化”最主要倡导者的张庚就抱怨,1984年底戏曲现代戏年会在上海召开时,一批戏曲学者故意用耸人听闻的语言提出,“‘戏曲化’已成为传统化、程式化、烦琐化、老化、僵化的代名词,它似紧箍咒束缚了从事现代戏创作的同志的手脚,成为现代戏发展的障碍”,因此,现代戏曲应该“大胆冲破‘戏曲化’的束缚,掌握时代信息,重视‘横向借鉴’,在戏曲表现形式上进行第二次革命”[5],这里说的横向借鉴,无疑是指戏曲应该借鉴话剧。
如果有现代戏曲,或者说戏曲现代化是不是指话剧化,现代戏曲是否仍能保持“戏曲化”特色,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什么是话剧化,什么是戏曲化?我们还是要从艺术形态的层面界定这两者的区别。无论话剧还是戏曲,都是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因此谈戏剧形态不能只看剧本,更要看剧本如何在舞台上呈现;戏曲如此,话剧亦如此。假如我们研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和成就,只谈老舍、曹禺和刘锦云、郭启宏,而不谈焦菊隐、林兆华,不谈于是之、濮存昕,那就很难说是在谈论北京人艺的话剧。所以,现代戏曲的“戏曲化”,剧本文体当然是重要的,戏曲化首先指戏曲剧本的唱词写作要符合各剧种的声韵格律(因无力掌握戏曲唱词声韵格律而鼓吹“现代化”的编剧当然是有的,但那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等等,但戏曲化显然不能只从剧本着眼,还必须考虑戏曲的舞台呈现。
多年来,人们用程式、虚拟、写意等等揭示戏曲表演的特点,但总令人感觉不得要领。20世纪50年代张庚最初提出“剧诗说”,当时指的主要是戏曲剧本的诗化性质,他晚年论及“戏曲化”时则越来越多提及戏曲表演的“节奏化”,体现了对戏曲舞台呈现特征日益深切的理解。阿甲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探索同样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在《戏曲表演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评论周信芳等大师的舞台表演时,阿甲多次反复、细致地说明表演时的锣鼓经,看似闲笔,殊不知这正是戏曲演员说戏时的习惯,而且他们教戏时也总是带着锣鼓经教。阿甲这样写当然有很深的用意,尽管他还来不及把他对戏曲表演的认识总结归纳为理论形态的表述,但他无疑直觉地意识到戏曲舞台呈现中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戏曲的所有表演都伴随着锣鼓经,总是在一种有规律的节奏中进行的,不仅戏曲的演唱有节奏的音乐,几乎所有表演都贯穿着鲜明且强烈的节奏感,无时不在的锣鼓就是在提示并强化这种节奏感。这样的表演才是“戏曲化”的,而多年来人们语焉不详的“话剧加唱”,正是因为丢失了表演的节律(焦菊隐显然也直觉地意识到戏曲的这一特点,所以他在北京人艺排演《虎符》时所做的“民族化”尝试主要是在表演中加上锣鼓经)。所以,戏曲剧目中很多重要的折子戏可以完全没有唱段,或由念白构成,或以武打为主,有完全不加唱念的起霸、走边等等,但是却不能没有锣鼓。齐如山说“鼓在戏里,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戏界老辈称,鼓为戏之胆”,从戏一开演,打鼓人就始终不能离座。[6](P416)同样是他通过对京剧演出的长期观察悟到的道理。
戏曲舞台呈现别具特色的“戏曲化”,就是这种具有特殊韵律感的有节奏的表演。它使戏曲在表演上形成如同韵文式的特点,因此和话剧散文式的表演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戏曲这种韵文化的表演有相对严整的格律,张庚称其为“剧诗”,更进一步说,戏曲的表演是格律诗,它与更类似于自由诗的话剧,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呼吁要用新剧取代旧剧,与其提倡白话文运动,推动散文化的新文学,实有逻辑同构的必然性。只不过同样都试图用看似更贴近普通大众的白话文书写的散文取代用格律化的文言(或仿文言)书写的韵文,结果却大相径庭,原因之一,是白话文运动所推动的是用普通民众熟悉的日常语言而非数千年来一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从事文学写作(即“语文合一”),随着教育普及,能够欣赏白话文书写的文学作品的受众在国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终至成为最具大众化的文学形态。而戏曲原本就是中国普通民众日常接受的戏剧样式,它虽然亦如同韵文,但这种韵文式的戏剧体裁长期为普通民众所熟悉,因而与民众并没有隔阂;而话剧在文体上看似更易为普通人所接受,民众却并没有欣赏话剧这种戏剧体裁的习惯以及美学准备。原因之二,白话小说原有悠久的通俗小说为基础,因此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出现了一批能娴熟地掌握这一文体并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小说家;而话剧在中国没有基础,因此要创作出优秀的话剧作品并不容易。从20世纪上半叶看,直到曹禺出现,中国才有基本合格的话剧创作(他在那个时代亦属凤毛麟角),等到第二位大师老舍出现,已经是数十年之后。其实在文学领域,小说与诗歌的命运也相距悬殊,缺乏传统积累的自由诗的发展道路亦十分坎坷,新文化运动后一百多年的今天,自由诗在普通民众中的接受程度仍很不理想,只不过现代公共教育丢弃了格律诗写作的训练,导致现在能用格律诗写作的诗人也越来越稀见。所以,现在的诗歌领域基本已经是自由体诗的天下,但原因却不是由于自由体诗更易为民众接受,而是由于格律诗的写作技巧已经失落。
新文化运动的锋芒同时针对戏曲与小说、诗歌等文学门类,小说领域新文学完全取代了旧文学,诗歌虽有改变却并不成功,格律诗虽然隐退,诗歌却因此丧失了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而戏曲除了增加了话剧这个舶来品之外,它本身几乎纹丝不动,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之前,戏曲的表演艺术形态和市场荣景依然故我,话剧虽在中国立足已稳,却只能依赖城市部分新知识分子形成的同温层取暖。诚然,如果话剧能如其应有的那样进入公共教育领域,如果从民国始,哪怕在1949年或改革开放后,我们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普遍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戏剧课程,结果或许就完全不一样。话剧表演这种散文化的舞台表达与戏曲表演的技术要求不同,无须自幼接受专业化训练,显然更有利于在大众中普及,面对戏曲它本该有白话文面对文言文一样的竞争力。新文化运动已经一个多世纪,如此漫长的时间段给了话剧如白话小说一样在大众中普及的机会,遗憾的是话剧错过了这个巨大且始终开敞的机会窗口,依然是极小众的艺术。而没有普及化的国民教育为基础,话剧的整体水平、尤其是表演艺术水平很难与戏曲相提并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戏曲“现代”成话剧,差不多就是要毁了戏曲这门艺术。虽然时有政治权力加持,戏曲界对话剧化的顽强抵抗仍成效显著,时至晚近,在戏曲界,“话剧加唱”被越来越多当成贬义词使用,坚持“戏曲化”更成为戏曲界的共识。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戏曲的近代发展都不得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以新剧取代旧剧的努力遭遇完败,让戏曲“现代化”或将传统戏曲转型为现代戏曲,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策略。那么,其成效如何?当代戏曲剧本创作确如吕效平所说,全面汲取了西方传统戏剧的“情节整一性”原则,因此与传统戏曲剧本文体差异明显。然而如果要证明当代戏曲发生了具有现代性的变化,不是借陈亚先、魏明伦、郭启宏对谭鑫培、梅兰芳的“革命与超越”来说明,只能是陈亚先等人与关汉卿、汤显祖的区别;然后还要看,在于魁智和谭鑫培之间、李胜素和梅兰芳之间,张火丁和程砚秋之间,茅威涛和尹桂芳之间,还有曾静萍、沈铁梅等人和她们的前辈之间究竟有哪些具有现代性的变化,如此才有可能定义现代戏曲。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世代更替中细微的变化固然有,但令人颇感欣慰的是,这些代表了当代戏曲高度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无不可贵地保持了戏曲的本体特点。假如舞台呈现和表演依然“传统”,找不到对谭鑫培、梅兰芳的“革命与超越”,戏曲又如何可能“现代”?
新文化运动推举白话文,简单地将韵文和散文分列为传统和现代的标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决不限于简单的文体之争。现代社会追求文化平权,这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将话剧定义为“现代戏剧”,当然有其理由,尽管用新剧取代旧剧的文化理想离现实还十分遥远。但是要让戏曲“现代化”的努力,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数十年来包括张庚在内,从未给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一份可操作的清单,除了吕效平所说“情节整一性”这个其实很不“现代”的变化以外,没有人真正知道戏曲在哪些方面“现代”了以及究竟要如何“现代”。从结果看,除了某些类似于要把交响乐“现代”成流行歌曲,把芭蕾舞“现代”成广场舞的呓语,现代戏曲仍是个悬浮在半空中的概念。
三
现代戏曲这个概念有两重可能的含义:一是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仅仅用于显示当代戏曲与传统戏曲形态有别,这里“现代”只是指其与传统的差异;二是作为具有价值内涵的概念,认为传统戏曲在新的时代行将被淘汰且必然被淘汰,因此要追求“进步”,使之演变为现代戏曲。如果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现代戏曲这个概念,它只是一种命名策略;但是在多数相关的论述中,“现代”都包含了对变化的鼓励与对传统的批评与否定。
如果撇开政治的和工具论的层面,仅仅从艺术角度看,在现代戏曲这个口号的背后,始终隐含着一个魔障,那就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化而来的文化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生物进化的模式平移到艺术的发展变化中,认为艺术也必将不断“进步”,新的艺术必将战胜和取代旧的,而且新总比旧好。在这种思潮的支配下,戏曲曾经多次遭遇死亡威胁,许多致力于戏曲“现代化”的人声称,如果戏曲在题材选择和思想意识等方面不做根本的改造,戏曲就将终结其生命,因为新社会的观众审美趣味变化了,传统戏曲“必定”会被时代淘汰。现代戏曲的倡导者就像传统戏曲命运的预言帝,他们不止拥有“观众审美趣味变化”这个想当然地虚构出来的唯一利器。对传统戏曲各式各样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描述,在此前提下对传统戏曲各种弊端的激烈批判,都成为戏曲需要“现代化”的理由。
对传统戏曲的一知半解甚至茫然无知,是批判传统戏曲和定义现代戏曲最大的障碍。诚然,今天的戏曲与一个多世纪前的戏曲,在艺术形态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只有深切了解传统戏曲的内涵与形态,才有可能清晰准确地判断与描述当下戏曲与传统的差异,假如说了半天“现代性”,结果却发现这样的所谓“现代性”在传统戏里比比皆是,岂非太令人尴尬。如前所述,那些显然是传统社会不曾有的技术因素,比如灯光、布景、音响的使用,被直接当成现代戏曲中的“现代”要素(从技术上说当然是对的);还有剧场形制的变化,剧场建筑质量的提升,尤其是观剧秩序的改变,这些也被作为“现代”要素(固然有现代的成分),但假如现代戏曲和传统戏之间只有这些表层的变化,只能从舞台美术或剧场角度审视,“现代性”就只是艺术的外壳。如果戏曲确实发生了“现代”转型,必定是涉及戏剧本体的,一旦进入这一领域,对传统戏曲的了解与把握,就成为判断戏曲“现代”与否的关键。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代主导戏曲发展的官员和理论家(更不用说主要从事话剧研究的戏剧理论家),基本上没有大量欣赏传统戏曲经典的艺术经验积累(如现在北京的戏曲评论家一样,尽管看很多戏,但基本上是各地送到北京来为评奖而创作的新剧目),更没有接续晚清民国时期的剧评家们留下的海量戏曲评论资源,由于对传统戏曲的陌生,他们多数都是先入为主地接受了现成的西方戏剧理论,轻信前人对传统戏曲之弊病的粗暴指责(包括一些坊间流传的牢骚话),提供的传统戏曲改造方略颇为草率,称其为盲人瞎马并不为过。
现代戏曲倡导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希望通过推行导演制(或编导制)等手段改变传统戏演员中心制的所谓“陋习”。20世纪50年代以来备受责难的演员中心制至少有两重含意:其一是指舞台演出时演员不完全按固定剧本演绎,经常自由发挥;其二是近代商业剧场创作演出均围绕主演的明星化现象。
戏曲的传统十分丰富而复杂,昆剧界从来没有演员中心制。不仅经典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始终得到强调,昆剧十二家门亦不像各地方剧种有明确的大小脚色之分。传统戏曲中的地方剧种如高腔、秦腔、梆子、皮黄等,确实普遍存在表演者自由发挥的现象,那是因为他们在民间尤其是广场环境中演出,多取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为题材,且表演者多不识字,当然无法背诵剧本。他们自创的唱词念白固然多有鄙俚之辞,但也正因此让民间化的想象与智慧融入其间,并且因艺人有充分的表达空间,而创造出无比丰富的舞台表演手段;清末民初城市戏曲的商业化潮流中,优秀演员的商业价值得到充分发掘,逐渐形成了演员中心(或曰主演中心)的演出体制,既带来了戏曲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潜在地诱发诸多问题,比如艺人间收入悬殊,配角作用被弱化,剧本编撰时过分偏重于方便主演展示其演技等。对演员中心制的批评,多少有编剧与演员为新剧目创作的主导权和利益分配等相互博弈的因素(晚近魏明伦提出“编剧主将制”正是其当代余波);然而,除几个最具规模的城市剧场(尤其是上海的四大京剧舞台和广州香港的几大粤剧戏院)外,围绕少数主演编戏演戏的现象远不像时人渲染的那么突出。更何况传统戏曲也讲“一台无二戏”的“一颗菜”精神,对演员中心制的批评用以针对商业剧场的演出体制则可,将它看成是戏曲的“传统”,未免离题太远。况且这些现象有得有失,不能一概而论,但它们的缺陷往往被无限放大,其积极价值则有意无意地被漠视了。而由此推动的所谓“现代”的导演制(或编导制)的普及,固然提升了戏曲演出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但又何尝不是当代戏曲演员自主创造性及表现力急剧下降的渊薮?
其次,是对戏曲艺人的职业操守的贬低。张庚1939年的表述颇具代表性,他说旧剧现代化的目标就是:
(一)坚持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向,要具体一点就是政治的方向;(二)坚持一个进步的创造艺术的态度(忠于创作,忠于剧的中心问题的表现,严肃,这些都是旧剧界的观念中所没有,至少是少有的)。[4](P243)
传统戏曲在数百年发展进程中取得了灿烂的文化成就,离不开“旧剧界”的无数戏曲艺术家的努力与创造,其中就包括“忠于创作,忠于剧的中心问题的表现”的严肃态度。具体而言,任何社会任何群体的职业操守都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戏曲演艺界长期受社会歧视、身处社会底层,容易滋生悲观和迷茫的人生态度,当然会间接地影响其艺术的呈现。然而各行各业都有贤有不肖,话剧界、影视界和音乐界美术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况且戏曲界也有“戏大于天”的传统道德规范,从来都不缺少对艺术严肃认真孜孜以求的典范。
有关现代戏曲的另一个误解,是说传统戏剧不“演人物”,因而必须将它改造为具有“塑造人物”之能力的现代戏曲。那种认为千百年来的传统戏曲只有一些简单、凝固、脸谱化的表达,“只演程式,不演人物”的观点,真是对天南海北的中国戏曲观众莫大的污辱,似乎亿万观众数百年来都傻瓜一样在看舞台上的戏曲演员摆弄一些凝固化的程式,这些表演都是“不演人物”的。即使我们不看近现代以来那些著名表演艺术家自己的经验总结,就从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对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的盛赞,从翁偶虹和阿甲对周信芳、程砚秋、郝寿臣、金少山等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成就的总结中,都不难看到优秀的戏曲演员对舞台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刻画。无论哪个民族的戏剧,故事、情感、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亦借此而显现。只要是流传久远的成熟戏剧,必定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欣赏者或有所偏爱,但是说戏曲表演都是脸谱化的,缺乏对人物个性化的表现,简直就太幽默了。
这些大而化之的言论,如同陈独秀批判传统戏曲小说尽是“富贵功名之俗套”[8],这是艺术批评的激愤之辞,如视为对戏曲传统的理论总结,并由此探讨戏曲发展的方向,就未免太不能令人满意。至于对传统戏曲中易性表演现象的批判,认为现代戏曲的成功之一就是改变了“男演女,女演男”的现象等等,更是十足的性别偏见。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70年来有关现代戏曲的讨论毫无意义,更不是说近代以来戏曲(包括舞台呈现)毫无变化。对传统戏曲持续的批评即使有诸多偏激之处,也依然产生了不少积极作用,至少当代戏曲从业人员在整体上对戏曲艺术的价值认知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戏曲表演这个职业的文化意义,有了更多自觉体认。戏曲是独立自足的精神创造活动而非工具,这一基于审美非功利性的观念日益成为行业共识(尽管现实利益的诱惑很难抵挡),这些艺术理念无疑是极具现代性的。而坚持艺术本体,强调戏曲要“戏曲化”,则体现了对戏曲独特的人类价值的另一层理解,从这一认知引向戏曲从业人员职业尊严的提升,不能说没有现代性的因素。
戏曲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当代戏曲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广场艺术为主,辅以少量厅堂艺术的多形态,向剧场艺术这单一形态的变化。相对隔绝、封闭的和性能单一的剧场成为戏曲呈现的主要场所。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里,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民营剧团在广场环境中的演出形态。戏曲的剧场艺术化包括戏曲演出功能的纯化,使之越来越变成可供艺术欣赏的精神创造,逐渐改变了戏曲被当成其他人类活动之附庸的现象。在北京的茶园时代就有萌芽、由1908年上海新舞台落成肇始的这一戏曲剧场化过程,让戏曲的价值与意义聚焦于舞台上演员的音声与形体的展现,观众进入戏曲演出场所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分享其中演绎的故事、人物和情感时获得审美体验。这种现象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至少不普遍,这一变化当然具有现代性意义。
戏曲的剧场化不仅体现为观演关系的这一决定性变化,同时兼及戏曲从业者的经营方式和观演双方的经济关系。重要的是,剧场化的环境让观演双方的主从关系完全逆转了,在整个戏曲的创作演出过程中,演什么和怎么演,主动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戏曲表演者手中。这种主动性表现在,即使戏曲剧团和演员仍会充分考虑观众的趣味,但那更多是一种经营策略,而不是因他们相对于观众的卑微地位所决定的;欣赏者必须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换来在特定空间时间欣赏演出的权利,他固然可在各类表演中选择,但选择范围依然是由表演者给定的。在剧场化进程中,戏曲从业人员的社会身份、地位和自我意识逐渐发生质的变化,而在戏曲活动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远远比成为国家干部或其代表人物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更内在地成为戏曲表演者获得职业尊严感的决定性因素。戏曲的剧场化进一步导致戏曲从业人员、尤其是演员的日常生活成为欣赏者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将戏曲置于社会的聚光灯下,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与改变了戏曲。
戏曲的剧场化倾向还有另一个观察维度,就是戏曲舞台呈现的精致化。从创作到演出的每个环节都精心雕琢,力求完善,尽可能使之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有机体,这是当代戏曲作品包含着丰富内涵的新趋势。戏曲台湾地区学者曾永义提出过“精致歌仔戏”的口号[9],正是大陆当代戏曲演进趋势的隔空回响;茅威涛说要让所有人穿着燕尾服进剧场看越剧,同样形象地表达了她对戏曲精致化呈现的强烈意愿。传统戏曲固然在每个细部都不乏力求精致的努力,但是全面与始终如一的精致化诉求,却是近代以来戏曲转化为剧场艺术后的新取向。戏曲的演出氛围从自由松弛的表演和轻松散漫的欣赏转变为认真严肃的“纯艺术”,原有的民间性状是被刻意剔除了的。当代戏曲的精致化倾向,其背景诚然与戏曲从业人员职业尊严感的提升及导演制的引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剧场化的戏剧经营模式与戏曲观念的变革所致。但我们还要看到,如果精致化就是现代戏曲的特点,它依然可以从昆剧的乾嘉风范中找到前身。戏曲从自由粗放变为规范齐整,这样的变化究竟是现代转换,还是回归古典?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
戏曲的当代演变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对戏剧的整体性前所未有的强调。如同吕效平所发现的,当代戏曲文本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普遍接受了对“情节整一性”的要求;但需要补充的是,当代戏曲不仅在剧本的结构上注重戏剧的整一性,在舞台呈现上同样极大地提升了整一性;不仅编剧将一部戏看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整体,演员按整部戏的思维设计自己的舞台表达;在戏曲音乐领域亦是如此,全剧从每个唱段的唱腔到过门、幕间曲和情绪音乐等等,均经过认真设计,并有使之成为整体的强烈主观意识。戏曲开始按“部”(或称台、本,总之是从头至尾的完整的一个剧目)为单位营销,观众在开演前进入剧场而在整部戏演出结束后离开,他欣赏的是相对完整的一台戏。
在尽可能保持戏曲表演本体特征前提下,戏剧的整体性呈现,确实是当代戏曲剧目及演出最重要的特性。戏曲的整体性首先是剧目的整一性,它部分与戏曲剧场化相关。在剧场化的模式中,戏曲的全剧作为一个独立且完整的单元呈现在舞台上,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它看似天经地义,其实不然,在此前近千年的戏曲历程中,无论杂剧还是传奇,折和出作为独立戏剧单元的重要性都不在全剧之下;每折或每出均为各自独立的套曲,完满自足(只有李渔等极少数剧作家例外)。元杂剧时代行院伶人在官府“唤官身”时只是表演剧目片段,尤以唱曲为主;昆曲与京剧主要演出形式是折子戏(民国时期梅兰芳的新戏体量仍与折子戏大致相当,他多次出国也从未演出过整本戏),每晚演出的十个左右折子戏相互之间并没有连贯性,观众更没有完整地欣赏整场演出的习惯;即使是以本戏演出为主的各地方剧种,观众任意进出广场式的演出环境也是常态,有演出“天光戏”习俗的地区与剧种,更缺乏以一个单位时间演出的戏剧为一个整体的意识。这些都说明戏曲以结构严整、叙述一个相对完整且独立的故事的剧目为整体欣赏对象的习惯是晚近戏曲演变的结果。欣赏习惯的改变和创作理念的改变互为表里,共同完成了戏曲形态的这一重大变化。
近代以来戏曲的演变,体现了编剧、演员、作曲(唱腔设计)和逐渐界入戏曲领域的导演等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从广场艺术和厅堂艺术向剧场艺术的转化是根本,整体化是最为全方位的演变结果,至于这些演变是否具有现代品格,实关乎我们对“现代”的定义和理解。
戏曲剧目的整体性和精致化无须改变戏曲的“剧诗”品格。戏曲如何才能做到既是“现代”的,又是“戏曲”的,这是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戏曲艺术家和理论家探索和努力的目标,我想这就是答案。至于如何从近现代以来戏曲发生的诸多变化中解析出现代性因素,恐怕还需要继续讨论;而要确保现代戏曲仍然是“戏曲”,还需要另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必须默认现代性是多元的,世界各国的戏剧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而不是全部变为一种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戴着多么亮丽的“进步”桂冠。
参考文献
[1]梅兰芳.解放一年来的感想[M]//梅兰芳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
[2]柯庆施.大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J].戏剧报,1964(8).
[3]吕效平.论“现代戏曲”[J].戏剧艺术,2004(1).
[4]张庚.话剧的民族化与旧剧的现代化[M]//张庚文录(第1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5]张庚.上海戏曲现代戏年会会后感[J].戏剧报,1985(3).
[6]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周传瑛.昆剧生涯六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8]三爱(陈独秀).论戏曲[J].安徽俗话报,1904(11).
[9]曾永义.论说精致歌仔戏[J].戏剧之家,2009(4).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投稿须知
《戏剧》是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艺术类学术期刊。本刊试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者来稿须标明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
2.基金项目(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3.中文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篇幅为150-200字。
4.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大致对应,长度为80个英文单词左右。
5.中文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6.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大体对应。
7.注释:用于对文章正文作补充论说的文字,采用页下注的形式,注号用“①、②、③……”
8.参考文献:用于说明引文的出处,采用文末注的形式。
(1)注号:用“[1]、[2]、[3]……”凡出处相同的参考文献,第一 次出现时依 顺序用注号,以后再出现时,一直用这个号,并在注号后用圆 括号()标出页码。对于只引用一次的参考文献,页码同样标在注号之后。文末依次排列参考文 献时不再标示页码。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
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专著、期刊、论文集、报纸等: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字母全部大写。书名、刊名用黑体。尽量避免中文与外文混用。
来稿通常不超过10000字。请在来稿上标明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电话,发送至学报社电子信箱:xuebao@zhongxi.cn。打印稿须附电子文本光盘。请勿一稿多投,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发现有一稿多投或剽窃现象,对我刊造成损失,我刊将在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投稿。来稿一般不退,也不奉告评审意见,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
《戏剧》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未单独开设任何形式的网页、网站。同时,中央戏剧学院官微上将选登已刊发文章。
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欢迎关注中华戏剧学刊联盟刊物公众号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

《戏曲研究》

《戏曲与俗文学》

《中华戏曲》

《戏剧与影视评论》
图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社



欢迎各位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中央戏剧学院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 “zhongxi_1938”,或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关注。
网站:http://www.chntheatre.edu.cn/
-
《戏剧》2021年第5期丨陈戎女:改编与重塑——跨文化戏曲中的女性人物及其意义
点击上方“中央戏剧学院”进行关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识别下方二维码查
-
活动预告 | 徽风晥韵进高校 黄梅戏曲进校园
徽风晥韵进高校 黄梅戏曲进校园原汁原味的唱腔 自然清新的表演让共达师生近距离领略徽风晥韵的独特魅力快和我们一起去期待这难得的文化盛宴吧10月27日14:30教学楼主广场节 目 预 告剧 团 简 介
-
上戏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服饰研究》 开题了!
上海戏剧学院潘健华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戏曲服饰研究》,是今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友情链接:
关注数据与安全,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https://www.ijiandao.com/
安全、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https://www.yaorank.com/
找律师打官司就上碳链网:https://www.itanlian.com/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林真yalan风偷喝了酒 于是脸红变成了晚霞[烟花]](https://imgs.knowsafe.com:8087/img/aideep/2021/8/26/4079a4120cfdb6feed6516c4b4c5ed1e.jpg?w=250)




 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